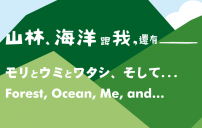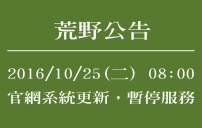愛在荒野流動
荒野有情,愛在流動 文/曾月美(荒野保護協會管理部專員) 圖/劉建隆(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自然名:松雀鷹) 一顆心和一條無形的線,出現一個人、二個人、最後是一群人,正是荒野高雄親子團二團用500多顆的蛋黃酥,串起志工與臺灣各地專職、人與土地的連結。 秘書長劉建隆(自然名:松雀鷹)為了想要瞭解各地分會秘書處理在地人、事、物,及在執行上哪些困難和徵詢建言,帶著我與另一位總會的夥伴同行,至各分會逐一拜訪串門子。兩天的時間看似蜻蜓點水式地到此一遊,實質的互動也有限,但象徵意義大於前,大早從臺北出發到桃園傾聽,新竹的午餐約會,下午二時許到臺中分會,半小時的對話真的無法聊得深入、僅是認識互動而已。 由於時間上的關係,直奔高雄前路過虎尾接雲林親子團一團前夥伴野薑花,她主要的任務是要到高雄感恩火鍋派對擔任大廚,交通與車程延,顯然野薑花只能幫忙。感謝高二團薔薇及親子團夥伴們的補位相助,荒野家人就是這樣可愛,熱鬧的場面、感恩的氣氛,帶動專職與志工之間的好氛圍,荒野、月圓、蛋黃酥、火鍋、感恩的心情……今年的中秋很不一樣。 第二天,傳愛蛋黃酥開始上路,一路往北到了臺南,享用臺南開元路的虱目魚大餐,十點多到了臺南分會,致上蛋黃酥也給秘書抽選愛心小天使,察看過分會會所場地後,松雀鷹約了分會秘書、南二團的夥伴和總會秘書、雲林夥伴一起午餐聯誼交流,更拉近專職與志工間的距離,也跨出區域交流的一大步。之後,摸索尋找到嘉義分會,分會秘書佩君已等候多時,除了蛋黃酥外,大大的擁抱更是有溫度。看到她獨自一人守著分會辦公室,這是要多大的溫情才能持續串起志工對土地的熱情與心力,確實是我學習的對象,如何能自在且盡心盡力地去執行這一成不變的工作。下一站雲林分會同樣是編制一位秘書——惠婷(自然名:薄荷)服務在地夥伴,懷著敬佩的心情遞上高二團愛心,希望這份溫暖給予夥伴加持。在雲林巧遇臺中分會分會長永滄,臺中夥伴的小禮物由其代轉,也因此我們有機會能讓永滄分會長領著我們進入斗六的老街、享用在地美食,人生幸福不過如此爾爾。 天黑夜行,來到新竹已是晚上十點了,蛋黃酥傳愛任務已進尾聲,由主任秘書靜珠代表收下後,再驅車趕往桃園分會,貼心的怡萍守在分會等候,時間已晚,沒有多做停留便繼續北返,晚上12點返回總會完成任務,如同灰姑娘般的準時。 這趟分會之旅,牽起大家的手、串起你我的情。對於工作執行上能有多大的改變可能是個未知,但肯定的是在每個人的心裡已種下一顆愛的種子,什麼時候會發芽?天曉得。不過,或許沒有預期的事情,反而會有更好的發酵。 荒野源自土地,一棵樹(協會)、枝幹(專職)、樹葉(志工)串起共為土地及環境守護的力量。愛在荒野流轉,期待今年不一樣的中秋,能帶動更多熱情注入荒野,也希望百年後的荒野更為茁壯。 溫情過後的感謝 文/陳紫緹(荒野保護協會管理部專員,自然名:紫陽花) 圖/劉建隆(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自然名:松雀鷹) 日復一日,季節春去春又來,這個世界不斷的運轉著,每天都是由不同的專業分工所組成。早上在人行道清掃的阿婆,早餐喝的一杯豆漿,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環節都是因不同人的付出而完整,對於看似理所當然的一切,其實暗藏著一股力量,只是我們都過於忙碌,幾乎快忘記它的存在,它的名字叫「感謝」。 9月12日星期一,這一天好像平凡無奇,但又與眾不同,「今天」就是老天給的特別禮物。荒野秘書長帶著我與同部門的月美,開車到荒野的各分會和秘書處的夥伴聊聊談談,此外,還有一個非常任務,必須到高雄領一份「超級大禮」,這是秘書長與高二團薔薇及親子團夥伴們為我們專職精心準備的中秋禮品「蛋黃酥」,我相信至今有許多專職因為這份禮物,心頭還滿是溫暖。 人與人之間,儘管有再多的差異與不同,唯一適當的回應就是「感謝」。別小看感謝兩個字,打開心胸只要透過、微笑、回應,或是你的出現,感謝將轉化為成感動,如此一來,這感動就會昇華成美好的祝福,也可以感受到自己和讚揚生命的宇宙有所連結。 還記得國文課本中曾出現的一句話:「要感謝的人太多了,那就謝天吧!」這是陳之藩的散文〈謝天〉中最為人耳熟能詳的名句,早成經典,這句話至今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之中。 滿是溫情的秘書處、感謝難得的緣、感恩大家的相扶持。祈願「感恩」與「承諾」陪著自己經歷豐富的人生。
臺北榮星花園公園棲地維護紀實
文、圖/許浩哲(荒野保護協會志工) 第一銀行松江分行本次參與荒野所舉辦的「守護榮星花園溼地活動」,於天氣晴朗的七月週六午後展開,每個人均帶著愉快愜意的心情參加,期許為這城市貢獻一己之力,守護這座復育螢火蟲的公園。 榮星花園位於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建國北路、龍江路與五常街所圍繞之區域,面積共6.5公頃,1968年由鹿港辜家開闢經營,基於辜氏家族對辜顯榮的紀念,辜顯「榮」,字耀「星」,所以命名為「榮星」花園;近年來對生態的重視,持續進行生態調查及規劃環境改善方式,並在生態池復育螢火蟲,成為臺北市區內少有、能觀賞到螢火蟲的公園。 在分行大家長高寶元經理、陳素蓮資副及湯懋春資副帶領下,所有參與同仁都準時抵達榮星花園,首先由公關室黃淑美經理向大家分享總行持續推動志工活動的努力成果,隨後由荒野保護協會志工介紹目前榮星花園生態維護情形,解說中不時看見松鼠們穿梭於大樹之間,似乎是為我們的活動進行喝采。 講解完畢後,大家開始披上毛巾、穿上雨鞋、戴上手套、拿起鐮刀往園區內生態棲地前進,由於外來物種會造成土質劣化及影響河流含氧數量,進而影響螢火蟲復育成效,所以今天的任務就是修剪水池旁的外來物種,再將這些雜草曬乾後回鋪於裸露的泥土上,既可保護土壤水分流失,也可作為土壤的有機肥料。 平時慣於坐在冷氣房工作的我們,真是難敵當日38度C的酷熱考驗,不一會兒就汗流滿面,分行主管們不時叮嚀大家要多喝水補充水分,預防中暑,真是揪感心耶!由於高經理平日待人視如已出,分行擁有良好的團隊精神,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同心協力整理環境,短時間已堆積出數座雜草堆,努力成果立即可見。 稍晚,大家將曬乾的雜草陸續回鋪到水池旁的泥土地上,順利完成本次棲地維護任務。最後,每個人輪流發表今日參與活動的感想,除了有感於勞動工作的辛苦外,更對我們居住的土地有了更深切的體悟,未來無論何時、身處何地,都要盡一己之力維護居住環境,讓後代子孫也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感謝總行公關室同仁及荒野保護協會志工協助,本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透過每個人小小的力量,不僅慢慢改善了我們生活的環境,也落實了第一銀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責任。
在親子團與大海之母相遇——從親海到愛海
文/林千地(荒野臺南親子團一團奔鹿團草原鹿,自然名:非洲象) 清晨初光,白色的光芒慢慢的映入眼前,小鹿值星官徐易廷(自然名:葉翅螳螂)帶領我們在觀汐平臺的「綠色隧道」裡晨跑,清晨的微風在黃槿林輕撫著我們的臉龐,也吹走心中湧起的緊張感。我們彼此有說有笑、自在地跑著,就像一群奔放的鹿群! 接下來,團長李淨榆(自然名:仙丹)帶領我們漫步在海邊,我們一邊走一邊看著海浪的潮起潮落,聽著海風跟我們說的小祕密。我們以靜默的方式與大海之母打聲招呼:「我們今天要來打掃海灘,希望活動順利進行,讓大海更加乾淨!」 這次由我擔任小組長,所帶領的民眾是宏遠紡織的員工,我先介紹如何進行ICC 國際淨灘和海灘塑膠微粒篩檢,並說明我們這組負責撿拾的垃圾類型是塑膠瓶蓋和塑膠瓶,民眾們就按部就班開始進行淨灘活動。在這裡我要給參加的民眾、我的隊友和我自己一個大大的掌聲,他們的認真態度讓我感到難以望其項背。我想這應該是需要我們心中努力地想表達愛海的心意,和他們也強烈地想為大海做一件好事,兩者兼具才能造就的成果吧! 淨灘結束後,我們引導民眾進行淨灘後的生活反思,如下: 淨灘時看見哪些垃圾? 它從那裡來? 我生活上可以做什麼改變? 牙刷。 飯店用完丟棄。 下一次去飯店時,自己攜帶牙刷。 生活中如何減少或不用一次性塑膠? 出門消費或用餐要自備環保餐具和環保袋。買東西前應該要先想是「需要」還是「想要」,再來消費。 塑膠微粒的旅行? 塑膠製品→ 被海水拍打→形成塑膠碎片→被海水拍打→形成塑膠微粒→小魚吃了塑膠微粒→大魚吃小魚→人吃大魚。 今天的淨灘結束了,耳邊傳來一首熟悉的歌,「大海啊!大海啊!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回想四年來在荒野親子團曾經參與過的各項海洋守護活動。 四年前,我進入了荒野臺南親子團一團炫蜂團。當時我只是一位天真年幼的小學生,並不知道大自然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什麼是淨灘,更不知道海洋面臨的問題,甚至連環境議題是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要去撿垃圾,也不知道海灘上有這麼多垃圾和塑膠微粒。親子團團集會的活動,讓我用心、用眼、用五官感受,為什麼我們今年撿了這麼多垃圾,明年卻依然有這麼多垃圾在海灘呢?這樣的海灘是大家想要的嗎? 當我加入南一奔鹿的大家庭。我也慢慢的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海洋守護活動:暑假時,我加入了荒野臺南分會的「少年影片導讀志工」,剛好第一次導讀的影片就是海洋影片。當時我負責導讀了「太陽之北」與「深夜之後」這兩部影片。 其中「太陽之北」描述了兩位年輕人在挪威度過冬天,從事他們最喜歡的衝浪活動。這兩位年輕人在當地撿了滿滿的垃圾,但那可是一個無人海灘,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垃圾?其實是因為全球有許多的海流,會帶著垃圾環遊世界。因此當你在海邊丟下一個垃圾時,其實在全球都有機會看到這一個垃圾。 而「深夜之後」是一群為海洋永續發展而努力的人;有無毒養蝦業者、不賣底拖網大小通抓的魚店老闆、依據魚類生長季節設計菜單的廚師。看到這些人守護海洋的方式,不禁讓我思考:即使食用海鮮,我們是否也有方法可以讓海洋永續發展?如果一直吃稀有的魚,有一天牠可能已經不再是「稀有」,而是變成「沒有」。影片結尾的一句話讓我十分感動:「親海,愛海,你自然就會去保護她!」 在荒野親近海洋的經驗有許多,例如:參加「徒步海洋達人」——段成龍叔叔(自然名:白楊樹)的親海小旅行,當一群小孩看到那一大片的海洋時,就立刻脫下鞋子,奔向大自然的懷抱,我想這就是所謂親海,思海,愛海;在奔鹿團集會,導引員張榮哲叔叔(自然名:蜘蛛)設計了一個青春夜行的活動,我們從鹽水溪下游走到出海口,再走到鹿耳門,這個活動讓我們看見,河流與大海之間的連結及相關的環境議題(消波塊、遺棄的蚵棚和許多垃圾……)。 四年過去了,我從親海到了解海洋,從行動到帶領引導反思。參加了這麼多海洋守護活動,下一步要做什麼?現在雖然還不知道,但是我永遠知道,我一定是朝著「親海、愛海、思海」,讓海洋更加美麗的角度去努力的!
11/04-11/30「山林、海洋跟我,還有______」展覽
臺灣是一座有山又臨海的島嶼。高聳的山群帶領我們將視角至世界級的高度,四周圍的海岸緊緊環抱著臺灣,串聯起我們與地球各角落的連結。山林與海洋以豐沛資源餵養著我們,然而人們久而久之習慣了,漸漸遺忘要關心身處的家園。 由一群愛好臺灣環境的環保素人所組成的荒野保護協會長期關注臺灣環境。在成立的21年中,透過教育推廣、荒地圈護等方式維護臺灣自然生態。2016年11月4日至11月30日於華山貨櫃屋的「山林、海洋跟我,還有______」的展覽,將以如何棲地守護以及關心自身的家園為核心來展示荒野這些年的守護成果。透過展覽,民眾會知道,想要環境改善,無需要成為環保生態專家,只要願意行動,都可以如同荒野的志工、會員一般,貢獻己力。 「山林、海洋跟我,還有______」展覽資訊[新聞稿/FB貼文/活動報導] 展覽日期:2016年11月4日至11月30日,每日11:00~18:00 展覽地點:華山貨櫃屋(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展覽活動:開幕彩繪 2016年11月5日 13:30~15:30 聯繫電話:02-23071568(荒野保護協會企劃推廣部) 媒體報導: 2016/11/06-自由時報〈彩繪動植物 愛上台灣 我們的家〉 2016/11/14-人間衛視〈從生活落實環保 華山文創"環保特展"〉 開幕彩繪活動花絮 展覽位置圖 如何抵達展覽地點
10/25 0800-1200 系統暫停服務公告
官方網站將於10/25(二)08:00至12:00進行系統更新作業。 維護期間系統會有短暫服務中斷,停止服務時間將視維護狀況提前或延後結束,造成不便請見諒!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配合!
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
文、圖/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臺灣研究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於2016年9月3至4日圓滿落幕,荒野保護協會受邀於大會發表專題演講《超越你丟我撿?潔淨海洋的挑戰與機會》,與會之產官學民各方代表也通過「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2016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為臺灣的海洋事務發展提出37個政策方向和具體行動。本期荒野快報節錄其中與協會關注之海洋議題相關的兩大政策面向中的12項建議,特別是海洋廢棄物與塑膠汙染在本次大會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 整合事權,潔淨海洋環境 (1) 以區域的觀點,整合海洋環保事權,由環保署統籌規劃,訂定〈海漂垃圾處理方案〉,協調整合交通部、內政部、農委會、海巡署等機關,加速推動潔淨海洋之整合事務與具體作為。 (2) 結合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與民間力量,籌措適當經費,研究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辦公室」,釐清海域污染之來源、組成與影響,訂定海域廢棄物清理標準作業程序,以及海域各類廢棄物處理與回收再利用辦法,使廢棄物成為資源。 (3) 儘速制定與公布限塑政策,加強民眾宣導,訂定有效辦法,以提高塑膠袋使用費用、限制民眾使用塑膠產品,並加速抑制塑膠微粒之海洋污染。 (4) 參酌國際海運或港口的相關公約規定,研究制定《水域清潔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或增修《海洋污染防治法》,以減少臺灣海域及港口之污染。 (5) 由交通部協助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廣工業港、漁港轉型為「綠色港灣」,並建立船舶型式、動力及電力系統、能源效率、燃料淨化、岸電使用、管理及設備操作等綠色船舶規範,以及國際通用的船舶綠色產品標準。 整合規劃,建立海域秩序 (6) 建議行政院確訂與公布預定進程,加速整合相關人力與資源,以宏觀格局,依法成立「海洋委員會」及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等附屬機關(構);或儘速邀集相關部會研商,積極立法,推動設立「海洋部」,以建立我國功能完善的海洋事務主管機關,從而引導國家海洋永續發展。 (7) 將「海域空間規劃與管理(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列為海洋與海岸管理政策的主要內涵,並以生態系統及永續發展為基礎,釐訂整合性海域空間永續發展推動策略,作為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海域空間規劃利用之指導原則。 (8) 編列充裕預算,積極進行整體性、長期性海域資源調查,建立科學用海之生態與環境基礎資料,作為《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及未來海洋資源地區與海域空間規劃管理之依據。 (9) 儘速研究制定《海域管理法》,依據海洋自然與人文屬性之基礎調查,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建立海域多元使用之新秩序;並由行政院建立海域多目標使用整合協調之平台與競合處理之機制,優先解決海上風場與漁業、生態保育及海洋環境保護間之衝突。 (10) 海洋及其資源為國家所有,人民依法取得使用權,惟政府應建立民眾與權益關係人參與機制,維護既有合法權益、傳統漁業及原住民傳統用海,促進海域永續利用與管理,建立共存共榮之友善海洋環境。藉由國內外海岸管理案例,致力宣導海洋保育之重要性,踐行資訊公開原則,並加強與地方政府及權益關係人之溝通,以落實《海岸管理法》的保育、防災及永續利用之目標。 (11) 海洋能源包括風力、潮汐、海流和溫差等,其開發涉及繁複法令和不同機關,相關部會應研商簡化其開發申請與審議之行政流程,並研究解決未來《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海床鋪設電纜等審議作業之重疊性。 建議 (12) 依據本次研討會專家意見及國際趨勢,我們建議政府相關機關應重視下列議題,擬定推動計畫,組織國內研究群組,並加強國際合作,作為臺灣邁向國際合作、共同解決區域問題的重點計畫:一、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之研究(Study on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 二、塑膠廢棄物之抑制(Control of plastic waste); 三、海洋能源及離岸風場之發展(Development of ocean energy and offshore wind farm); 四、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五、海洋保護區網絡之建構(Establishment of MPA network);六、永續漁業之合作(Collabor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2016年9月4日「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所有與會者一致通過。)
沙灘上,要抓寶還是撿垃圾?——淨灘直擊的寶可夢現象
文、圖/溫郁琳(荒野保護協會企劃推廣部專員,自然名:溫帶雨林) 給 親愛的寶可夢訓練師: 抓寶的同時,自己垃圾不落地,也順手帶走海岸上的垃圾…… 讓神奇寶貝們在美麗的海灘跑跳(Gotcha)! 讓眾訓練師們在潔淨的海灘冒險(孵蛋)! 風靡全台的「精靈寶可夢GO(PokémonGO)」遊戲,讓宅在家中的現代人走到戶外。但是,身為神奇寶貝訓練師的您,抓寶的同時,是否讓自己的垃圾落地了?還是,有順手帶走沿途的垃圾呢? 九月的週末在新竹南寮漁港辦理的淨灘活動,我們直擊到了寶可夢訓練師奇景。天候不錯的上午約七點至八點,此處群聚了許多民眾,捧著手機漫無方向地遊走著。由於民眾的數量遠遠多於淨灘報名人數,讓當天淨灘活動上演了一場不尋常的畫面:沿著海岸線上的堤防,沙灘上是組成小隊行動的淨灘夥伴,拖著大大的垃圾袋,低著頭默默撿拾、分類垃圾;另一端的草地上,是為數眾多的訓練師緊握著手機,低著頭以緩慢速度在人群間相互穿梭。 同時,我們透過「淨灘達人LiveShow.海洋靠你救」Facebook 直播活動傳遞第一線的觀察,因為再多的文字說明也抵不上真實影像的衝擊。這項活動是為了鼓勵每位關心海洋的個人,透過臉書直播功能,以自己的視角與影響力,帶領關注荒野Facebook 專頁的11 萬名粉絲們從不同角度認識、瞭解淨灘。目前活動仍在進行中,歡迎前往活動頁面,瞧瞧我們在南寮漁港直擊一幕幕海邊撿不完,陸上又繼續丟的景象。 沙灘上的垃圾 陸地上的垃圾 所以,踏上沙灘的我們,要抓寶還是撿垃圾呢? 我們肯定寶可夢的魅力,讓許多民眾展開行動走出戶外;更期待神奇寶貝訓練師們可以真正地觀看身處的環境。跳脫虛擬的趣味,面對真實的現場,好好思考如何與自然生態相處,而不是在虛擬載具中構築另一處美好世界。
大肚山守護夏日紫斑蝶活動
文/郭秋幸(自然名:小白鷺) 圖/陳嘉瑞(自然名:蟲言蟲語)、蔡佳真(自然名:赤皮) 大肚山定觀點介紹 荒野臺中大肚山組從2015年11月起固定在臺中市瑞井社區進行定點觀察,瑞井社區雖然距離臺中市中心不到30分鐘車程,但仍保有傳統農村濃郁人情味和懷舊的土角厝。 大肚山台地降雨量低,由鵝卵石和紅土所組合的地質相當不保水,成為全臺最乾旱的草原生態系,瑞井社區三口井是早期山上自來水系統未普及前主要的飲用水來源,其水源來自於水井上方森林的滲透水,倘若森林遭受破壞斷絕水源,這三口井便會失去其功能。當然在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下,瑞井居民已經不需要前往三口井打水生活,而這三口井周邊的小徑便轉型成為社區營造中,居民休閒運動的步道。 荒野大肚山組夥伴在蔡志忠老師(自然名:大頭茶)的帶領之下,在三口井上方森林持續二個月的植物調查,經由老師分析的資料發現,森林裡調查的樹種因為氣候與土壤乾燥,所以生長特別緩慢,透過比對歷史資料發現,平均樹圍七年只有長胖0.49公分,所以森林裡的每一棵植物都彌足珍貴。 守護紫斑蝶活動源起 大肚山除了有其特殊的草原生態系植物,同時也是紫斑蝶遷徙的重要路徑,四、五月份定點觀察時,夥伴們發現,成群結隊的紫斑蝶不斷從我們身邊與頭頂上飛過,在這二個月期間,瑞井社區居民也紛紛捎來訊息,通知夥伴們紫斑蝶湧現的盛況。 持續半年的定觀活動也加深了夥伴們和瑞井社區居民的互動,透過多次交流對談中,瞭解居民對除草劑和除蟲劑的使用習慣與蚊蟲影響生活環境的困擾。基於對生態平衡的考量,夥伴們討論取得共識後,計畫舉辦第一場瑞井社區居民的推廣活動。 為了引起社區居民和小朋友能對瞭解周邊生態環境的興趣,大肚山組的夥伴透過會議討論決定以紫斑蝶為起點,透過社區內的推廣活動喚起居民對社區周邊自然環境的關懷與重視。 守護夏日紫斑蝶推廣活動過程 大肚山組成立時間短,夥伴人力不足,面對此推廣活動的策劃、安排與人力動員,難免感到惶恐和擔心。籌備過程中,不僅受臺中分會長游永滄(鵂鶹)和分會夥伴的支持,中部各定觀點夥伴紛紛提供支援(勝興組、霧峰組、大坑組、合歡山組和彰化組),給大肚山組最大的鼓勵和實質的支持,並積極參與籌備規劃會議與活動預演。 活動開始前的一場大雨,讓大家心中忐忑不安,待活動開始時間接近,居民陸陸續續加入,心中那顆大石頭終於放下。各定觀點夥伴到場相挺,提供活動創意,且熱情活力投入,我們一起共同完成這場貼近社區居民和社區環境的推廣活動。並透過此推廣讓社區居民瞭解這塊土地的獨特性與生態的珍貴性。 結語 荒野臺中大肚山組選擇在一個農村社區作為定觀的起點,雖然曾為定觀點的選擇是否適當而徬徨過,但透過小組會議凝聚大家的共識,讓大肚山組走出和其他定觀點不一樣的風格與目標,以持續記錄的物種調查進行觀察,加入歷史文化層面的田野調查來瞭解這片土地。並透過與居民的互動傳達荒野對自然環境尊重和守護的理念,荒野臺中不僅走入荒野,也走入社區,希望這股愛護土地、尊重在地文化的力量,能透過持續的定點觀察活動不斷擴散、持續傳播。
守護環境,從1開始
文/陸淑琴(荒野保護協會棲地守護部專員,自然名:黑眶蟾蜍)、圖/荒野保護協會 自從318 學運以來,公部門比以往更積極地邀請公民參與政策制定與公共建設規畫的前期討論,如營建署針對國土計畫的公聽會、水利署針對南部水資源管理的工作坊等。雖然公告訊息的方式還稱不上友善便民,但獲得資訊的時間已提早了幾天;超過會議時間才收到公文,或是動工了才知道有工程施作的情形也少了一些。 推動公民參與,中央部會比地方政府還要開放許多,如環保署的環評會幾年前在環保運動前輩的努力下,除會議資料在會前於網路平台開放下載,記者也可進入會議中進行影音記錄、轉播,結論表決時記者仍可留在場內;民眾也只需現場換證即可進入會場旁聽及登記發言,如旁聽人數超過會場容量,便另闢空間提供會議現場影音轉播供旁聽。反觀高雄市政府在8 月31 日召開的環評大會,卻走了回頭路:除嚴格限制與會民眾人數外,會場中禁止錄音、錄影、拍照、轉播;當天開放民眾發言提問的人次共12 位,每位3 分鐘;發言加旁聽及記者(亦不得攝、錄)共20 位,其他有意旁聽的民眾僅能在場外守候。除此之外,會議中要求發言皆未獲得主席同意,若要取得旁聽或發言權,僅能於會前規定時間內下載報名表單填寫個人資料及發言內容並限傳真回覆,且由府方人員電話通知才算報名成功;會議前依報名清單換證,於入口處確認佩戴發言證或旁聽證者才得以入場,如此嚴格把關,頗有演唱會憑票入場意味(或憑良民證入場),不得讓人更好奇限制如此嚴格的背後原因。 在自然資源有限的臺灣,公共建設規畫及政策制定,皆與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息息相關,如何達到平衡需要透過討論取得共識。公民參與讓決策者能獲取更多面向的資訊,避免依據片面資訊進行決策,讓環境永續經營,而非僅落實部份人的正義。 公聽會、審查會、說明會皆在平常週一至週五上班日進行,若要每場參與實在不容易,且讓人擔心,若不是自己的專業,該如何回應?換個角度想,為自己請一天假,把時間用在公民參與,不為任何團體,就為多瞭解自己生活的環境會遭遇什麼樣的未來;也許不是自己熟悉的領域,無法提供專業建議,但比起僅短期停留協助規畫的顧問公司,在地長期居住、生活的您,一定更瞭解實際狀況,甚至於未被專業人士察覺的問題;更可以透過會議裡,民意代表(議員、鄉長、立委)、審查委員的發言、專家學者的觀點或是在地居民的訴求,或從其他人提出來的問題了解彼此關注的焦點有何不同。除此之外,每個人都可成為資訊透明的推手,把您獲得的會議訊息傳遞出去,或在手機結合社群網站即可網路直播的現在,讓無法親自與會的人也可以透過轉播掌握會議即時動態。 「從1開始,守護環境」。 推薦給關心生活環境的您: 1年請假1天參與1場公聽會、環評會、說明會 1季踏查1次荒野分會守護的棲地 1個月參加1場環境講座 1週觀看1 集公視「我們的島」節目 1天關注1 則環境議題新聞 1餐包含1項友善環境的食物 1年捐出1%所得給環境守護團體
從解說教育到棲地守護
文/宋明光(荒野保護協會解說教育委員會新任召集人)、圖/荒野保護協會 今年6月在新莊歡喜熱鬧中慶祝成立21週年之際,協會也由最初始臺北成立時的解說教育工作委員會發展到至今11個分會12個工作委員會。荒野數千位志工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服務領域,各自依任務需要而發展出不同的訓練與小組。組織不斷擴展與開枝散葉,志工分工合作,但一切的基礎本質,仍是以協會宗旨「棲地守護」為基礎。我在此刻承擔荒野解說教育工作委員會召集人,除了承續過往前輩所留下的穩健基石,也期待能為解說教育注入更多元的可能與開展。 自然解說員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如果問「荒野解說教育與一般的解說教育有何不同之處?」,回顧荒野二十一年來的解說發展脈絡,解說員結訓後的「定點註冊」制度,應該是奠定解說員能在地深耕的關鍵。藉由定點觀察,讓剛結訓卻對生態知識還很初淺的解說員有一個長期自然觀察與學習的基地,每一筆自然觀察的記錄,也成為棲地守護的基礎資料庫。解說員在定點中透過推廣活動,來邀請大家加入協會或是與社區結合,有不同多元的發展,提供解說員服務的平台。荒野解說員散佈全國,全國有五十多個定點,這就是透過了個人、定點生態、分會組織之間的連結,構成環境守護的點、線、面。每一個棲地定點,無需水泥硬體設施,就能完成遊客中心的解說導覽的功能,這也就是「定點=無實體自然中心」的概念。 在過去您所聆聽解說的經驗中,一場精彩或是讓人感動的解說,它的內容涵蓋了哪些元素呢?大部份的人覺得印象深刻的部份,應已超越知識的層面,而是在解說或引領體驗活動之中,勾起了我們內在心靈的共鳴、或是生命經驗的感動與啟發。也因此,荒野的解說內容並未侷限於知識,也同時融合了開啟感官與自然連結的「生態心靈風」、透過體驗與分享探究主旨的「探索體驗教育」等。「法無優劣,應病者良」,不管用任何方式任何技巧,只要有效、能影響人、能感動人,就是最好的方法。期待透過不同的解說引領與活動方式,讓民眾在認知、情感、體悟中對環境疼惜與認同,最後願意付諸行動,友善、回饋、守護我們的環境。 荒野解說教育的發展,在招訓時的所設門檻並不高,我們期待透過素人解說員的參與,讓更多對生態有興趣的人有機會一起來關心環境、為環境發聲。願心、熱情、持續,就是我們尋找夥伴的期待與標準。荒野的解說技巧,也由原本單純的單槍匹馬「隨機式解說」,發展到群體作戰、心法陣法兼修的「天龍八部」,在做中學,並融合了解說教育與棲地守護的實踐。 未來以「自然達人」、「EEE體驗式環境教育」、「生態心理學」為荒野解說模式的三大推動主軸:自然達人仍以定點自然知識為基礎,累積生態資訊的傳達,近年更發展成在每年地球日時的全臺定點聯合棲地調查,讓各定點的記錄整合成為有更意義的生態資料;EEE體驗式環境教育希望更有系統的引用體驗教育的方式,結合生態遊戲,並強化帶領反思的技巧,融合成具體驗教育風格的環境教育;在氣候強烈變遷的時刻,大地受到許多的創傷,我們的解說要融合大地的啟示發展環境意識的體驗教育;生態心理學則以John Seed所傳授的「眾生大會(Council of All Beings)工作坊」為代表,透過活動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創造直觀及情感上的深刻連結,並宣揚荒野地保護的心靈意義。 多元化的解說模式,提供給個性特質不盡相同的解說員、風土文物各異的定點,可依自己的特色來選修。加上過去發展過輻射式解說、主題式解說、主旨式解說、體驗式解說、心靈風解說、療癒系解說、解說三面向(認知、情感、行動)等教材,堪稱荒野解說的天龍八部。未來,因為更多夥伴的投入、創意與奉獻心智,將有更多蛻變演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