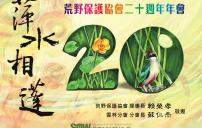那一年,我當炫蜂團團長
文、圖/白宜錚(荒野臺南親子團二團團長,自然名:唐棉) 與我一起「蜂」 決定一瞬間,豐厚一輩子 記得去年3 月前往臺東擔任荒野臺南分會第三期炫蜂團導引員基本訓練的火車上,林美玲(自然名:綠綿羊)、黃克穠(自然名:穀精草)輪流與我跟王福群(自然名:無尾熊)「聊天」,主要是為了找出下年度的團長,當時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擔任,一方面考慮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伍芷葳(自然名:喜樂蒂)要升國三深怕疏於照顧她。回家與家人商量後,老公伍清欽(自然名:大黃蜂)很支持我,他覺得能夠有不同的學習機會,要勇於嘗試;女兒喜樂蒂則說:「是我要參加會考,又不是妳要參加會考,不用考慮我!」想想也是喔,我又不能為她讀書;兒子伍峻寬(自然名:小麻雀)很直接的說:「不行!這樣妳陪我的時間就會變少了!」幾經考量下,讓我SAY YES 的主因是「身教」,大人常常跟孩子說要勇於嘗試、遇到困難要想辦法去克服,同樣的情況在我身上,我怎麼可以選擇逃避呢?於是我鼓起勇氣接任了團長。 自我成長篇 上述提到我自認能力不足,因此從決定接任後便積極、認真地參與各項課程,不論是分會舉辦的第12期自然觀察班,或遠赴桃園參加親子團總團舉辦的導引員第9 期進階訓。在這些訓練中,結識了一群同樣熱愛大自然的好夥伴,當我遇到問題時,他們成為了背後的智囊團,臺南親子團二團的官網就在友團的協助下應運而生;生平第一次擔任講師,就是進階訓的講師,對於菜鳥的我而言,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些經歷從文字上看似簡短簡單,但對我而言,背後的努力可是白了許多頭髮、失眠了許多夜晚才完成。 團務篇 對我而言,在團務上要學習站在親子團的小蜂、大蜂、導引員、團長等不同角色的夥伴溝通,身段要柔軟接納各方的意見,做抉擇也成了一門學問。回首這一切,證明了「付出越多的人,收穫越多」,這些感觸唯為實際參與才能體會。親子團本是個良善的團隊,臺南親子二團炫風團的夥伴又很好相處,導引團隊與育成會配合度相當高,身為團長似乎只要出張嘴就好了,當團長好處多多,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3 次:歡迎大家勇於自我挑戰喔!歡迎大家勇於自我挑戰喔!歡迎大家勇於自我挑戰喔! 家庭篇 小麻雀很黏我,當我要離家過夜時,最初他從前一週開始夜夜啜泣,我會找燈光美、氣氛佳的時機與他溝通,孩子的適應力其實很強,下一次出門變成前三天開始哭、再下一次可能是前一天,習慣後就是嘴巴上碎碎念而已。我想這是他成長的開始,如果沒有這樣的轉變,就沒有機會看到孩子的潛力,也讓他知道自己可以獨立。 我是個很容易緊張的人,喜樂蒂一言點出我的盲點,每個人各有各的角色,不需要為誰遷就自己。現在的我很慶幸當初做了正確的決定,否則依照我的個性,應該會常常在她身旁碎碎唸,反而可能增加親子關係的緊張。過去這段日子,我已自顧不暇,沒什麼餘力管她,甚至常常忘了在聯絡簿上簽名而被她唸。說來慚愧,當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晚上送便當,讓她有健康的身體應試。 大黃蜂是個無可挑剔的好老公,他只要我做我自己,給我很大的空間,從不要求我做家事或煮飯,這一年來我真的花不少時間在團務上,家裡難免疏於照顧,他總是默默的補位,甚至在我基訓結束回到家中時,他帶著兩個孩子做一頓豐盛的晚餐等著我。在我低潮時,他又像是我的心靈導師,陪伴我並分享工作上的經驗提供我思考的方向,我們夫妻倆因此有了共同的話題,精神上親密的程度拉近許多,也從不同的角度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這一年多來,謝謝夥伴願意給我機會為大家服務、包容我、與我一起「蜂」,你們每一位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貴人,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陪伴,我的生命因此更加豐厚。唐棉正式下台,深深的一鞠躬。
生命的熱度,存在於自然與人群和諧共處之間──氣候變遷小組出發!
文、圖/蘇雯祺(荒野保護協會氣候變遷小組,自然名:高蹺鴴) 圖/荒野保護協會氣候變遷小組 悠悠千古,生命與萬物在這顆星球上棲息,交互影響,多次劇烈的改變讓星球的樣貌隨之更迭,因而在現代我們不見恐龍,不見祖先。遙遙歷史中變換的樣貌或許無法親眼見證,但在時間輪軸裡,風與浪仍不斷讓砂石滾動,水與空氣的旅程從生物到土壤,在短短幾年間僅見小小一隅,即足以令人屏息。 人們的餐桌上,食物鮮甜可口,烈日下,樹蔭涼爽,大自然孕育萬物及渺小的人類,其美麗無庸置疑;與此同時,我們卻也看到這顆星球正在怒吼。雨量暴增,乾旱降臨。天災,讓萬物措手不及。科學家說,親愛的地球正在用自然的方式,告訴人類活動的力量如此巨大。我們的環境,正面臨氣候變遷的衝擊。 2015年4月底,臺灣的旱象尚未解除。有人從住家前來,有人自校園出發,有人甫步出辦公室,於各地生活的人,凝視當下,思索過去,遙想未來,我們對氣候變遷尚有疑慮,卻也堅信,即便會跌跌撞撞,仍舊得跨出舒適圈,開始嘗試。於是,大夥兒一一踏進詔安街一處的地下室,看著牆面上搖曳的萍蓬草及徐仁修老師的諄諄話語,開始這段氣候變遷志工培訓課程。 剛進荒野的我,總聽夥伴們提起,氣候變遷小組是荒野中最年輕的群組,首次開設的課程,在隊輔及學員的心中多少有些遲疑,但忐忑不安的不確定感與堅定不移的信念,同時趨動,還是下定決心,放手一搏,不甘讓環境遭受過度的影響,也準備在歷史造成的傷痕中,好好調適。 回想起首次的相見歡,即感受到荒野以獨特的帶領方式,讓彼此初步認識,找到自然的靈魂,挖掘到每人皆是不同背景的獨立個體,並都是可愛親切。荒野,好像總以神奇的魔力,將這些在乎環境的人齊聚一堂。在一段一段專業的課堂上,龐雜的數字與專業術語沖昏了我們的腦袋,科學、歷史紀錄轉達多少天災人禍,怵目驚心,但與此同時,亦感受到老師們投入大量的心力血淚,可能只為人類不了解樹木之苦,可能只因擔心原始而友善的農業將沒落,可能只為讓荒野回到人們的身旁,可能只為傳統節氣遭人遺忘,這種種讓臺下的我們心中既是不平,又是感動,有時,偷偷看見夥伴忍不住落下淚來,自己的眼眶也濕潤起來。 每每在這些知識與故事充耳之後,內心滿溢能量,但當低頭看見單薄的自己,又要轉入失望,見這一落,身旁的夥伴馬上拍拍我肩,熱情給予鼓勵,不吝分享生活中所見的狀況,又是付出真誠的努力,讓我甩開灰心與徬徨。溫暖常在的荒野,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更將人與人之間緊密連結,於是我才知道,不論自然中的荒野,或是人們所待的荒野,其中的每一份子即是如此互相扶持。 以輔代訓的我,一邊暗中聆聽著資深荒野夥伴們的經驗,讚嘆其過人的專業、意志力與執行力,一邊仰望臺上教師的風采,一邊向十八般武藝的學員們學習,短短兩個月,好似就吸收到多年精華。除此之外,被困在都市叢林有些不習慣的我,也藉著課程安排,走訪城市不遠之處的秘境,在農場裡看到城市小農們的努力,在臺灣北端見到壯闊的水梯田,這才發現,自然的奧妙始終吸引著我,老祖先的智慧讓我敬佩十足,但這些卻長期莫名地被隔離著。同時,我也跟著憂心,人類與萬物面臨氣候變遷的挑戰已然到來,農民與滋養萬物的土地,將無法繼續漠視,我們必得開始行動。 時光飛逝,第一次的培訓課程在一片蛙鳴蟬叫中結束了。過程中碰撞不時,調整不斷。這段時間裡我們瞭解到,氣候變遷的艱澀複雜不該是阻饒我們面對的理由,氣候變遷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就如同自然界的食物鏈,一環扣著一環。其實,在每日的餐桌上,就可見其與生活的聯結:食物的碳足跡、食材的在地性與當令的重要性,都是左右氣候變遷的小螺絲釘。其實,萬物在其底下乘涼的大樹,固定了大氣中的碳,但樹木的生命卻被人類力量箝制的喘不過氣,甚至喪失生機,我們痛心疾首想要改變、翻轉這樣的現況。 未來我們希望開設「餐桌上的氣候變遷工作坊」、啟動「樹木調查」,提高大眾對氣候變遷的關心度,同時減少無聲地默默付出的朋友——環境的無奈與憤怒。這是顆小小卻堅毅的種子,讓每個人從改變自己開始,一步一步,減緩衝擊並調適。我們知道,未來或許緩慢而艱辛,但是含苞待放的花朵,將以溫柔而勇敢的意志,持續向前。
成為海灘的小小守護者
文、圖/蕭裕聖(荒野臺南親子團一團,自然名:貓頭鷹) 其實這是個突發奇想的想法,因為每個禮拜六、日我都會帶著一家四口出外遊玩,玩 了一段時間發現從臺中以南好像已經都走遍了。今年5月23日星期,我突然靈機一動,利用林佩瑛(自然名:香蜂草)去擔任親子團小蟻團基本訓練志工時,我和兩位小朋友蕭敬學(自然名:抹香鯨)及蕭敬嘉(自然名:大翅鯨)商量:「我們去海灘撿垃圾好嗎?」他們倆也糊里糊塗都說好,其實我不清楚他們是真心回答,還是只是隨便回應。我們首次選定的地點在南部興達港火力發電廠旁的一處海灘,不是魚市這個方向而需從高雄永安進入。 為何會選擇這個海灘呢?其實是場無心插柳,有一天,我、抹香鯨及大翅鯨四處探險,突然發現這個地方,由於位處偏僻只有釣客才會到這兒,兩個孩子在這裡玩了30分鐘,與這片海灘培養了感情,所以選定此。 星期六當天,我們大約8點30分出發,大夥們準備了5個家用的小垃圾袋及棉手套,由於第一次行動怕準備太多、太大,做一次就嚇到沒有下次。出發後突然下起大雨,兩個孩子在車上擔心不知等會兒該怎麼辦?我提議先開車去看看吧!如果雨勢太大就當開車郊遊。沒想到一到目的地,老天爺真幫忙竟然停雨了,最後連烏雲也跑掉了,老天爺一定知道我們有做的決心。 因為海灘上的垃圾太多,加上我們僅帶了5個垃圾袋,因此此次「海灘消滅垃圾大作戰」的目標以塑膠類垃圾為主,以邊走邊玩的心態,總共花費約為80分鐘,以直線距離估算約走了100公尺,撿拾完後我們就開開心心地開車到岡山休息吃飯。我們3人討論了今天的心得,以下是節錄的對話: 大翅鯨說:「撿了5包垃圾,沙灘上還是這麼多垃圾。」 抹香鯨回答:「撿了5包垃圾,世界上就少了5包垃圾,不撿它永遠就在那邊,而且有可能還會增多。」 我說:「我們撿的5包不是垃圾是黃金,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倆都愣住不知如何接話。 我又說:「我們幫沙灘撿走垃圾,就是無形的黃金,對大自然是有益的,因為這些塑膠物就不會流到海裡,被海洋動物吃掉。」 貓頭鷹對抹香鯨及大翅鯨說:「我們都看過一部電影『那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主角柯景騰有一段台詞:我想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因為有了我,讓這個世界,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而我的世界,不過就是妳的心。而你們今天所做的『海灘消滅垃圾大作戰』,就是因為有了你們,讓這個世界,而有一點點的不 一樣,這個世界需要的正是你們的心和行動。」 我會開始做這件事,起因是荒野給我保護環境的種子,雖然每個月親子團的團集會次數不多,因看到荒野的其中一項任務「關懷海洋永續」,啟發我去做一些實際的守護行動。 起初我相信要實現目標必須從戰略、戰術及戰鬥3個層面執行,由上到下是戰略指導戰術,戰術指導戰鬥,由下到上是戰鬥支持戰術,戰術支持戰略,也就是點連成線,線連成面的關係。「荒野的使命與目標就像是戰略(面)」,「個人的執行就像是戰鬥(點)」,所以必需先從每個人做起,不斷的執行(戰鬥),才能從局部勝利到全面勝利,完成最後戰略目標,就像小火光一樣,有許許多多的小火光集合在一起,就能照亮一切。 再者,我想要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些甚麼?從小到大不斷聽大人、別人告訴我該怎麼做,但聽過後有做嗎?沒有,大多都是左耳進右耳出,就像古人說的「知易行難」。所以,我認為現在孩子們已聽了很多,聽的都是別人給的經驗與要求,故最重要的就是引導他們做,只要專注做一件有益的事且要持恆,讓他們從做的當中體驗出屬於他們本身最真實的感受,而不是別人給他的,這樣他們才能一輩子的記住,並有可能再次發揚光大。 另外,我也藉由此次的小活動做實驗,一家四口都成為白老鼠,實驗題目是「修補破窗理論的實際運用與效果」,現在我跟成員達成共識,每月挑選其中一個週六或日,利用上午1至2小時到海邊淨灘,我想試試在這過程中,當別人發現這片沙灘是有人在淨灘時,如果他想丟垃圾的時候,是否會制止不要亂丟;進而啟發他的心,也跟著我們一起做,即使他只撿走了一個垃圾都很好,因為對這片沙灘來說就少了一個垃圾。 期許全家能相互鼓勵並持之以恆,我也會有偷懶不想做的時候,就得靠家人的提醒、勉勵,激發一直想做的心,才能一直走下去做對的事。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因為有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才有小小的感想與大家分享、一起努力,為地球盡一份我們小小的心力。
2015 鐵馬環島倡議PM2.5,BYE ! BYE !
文/張秋子(荒野雲林分會推廣講師組長,自然名:路路通) 鐵馬環島看似結束,其實是另一活動的開始!8 月22 日- 23 日荒野廿週年年會慶即將舉行,目前已經緊鑼密鼓積極展開活動運作了。 環島的12 天,除了沿途關注當地的空污指標紀錄,親身感受實際的空氣品質,盡東道主的真誠將邀請函送達各分會及連絡處,也同時迎接各地分會的陪騎引導與體力加持支援,感謝之情意難以一一敘及,只能殷切期望熱鬧的8月能再與大家相見並答謝。今年年會慶將廿年荒野人走過的歷史與努力,以不同活動形式呈現,挑起荒野人內心的初衷與記憶。雲林分會是荒野最年輕的分會,有著總會夥伴的相挺支持,憑藉著雲林夥伴們的一股衝動與傻勁將工作完成,期待新舊夥伴們一起來參與回憶。 空氣品質必須長時間關注,水源與土壤也需要關懷,荒野人長期綿密的觀察與記錄當地生態活動,僅佔了臺灣少數的點面,但只要減少人為的干擾大自然可自行修復原貌。反而是人群聚落的點面更需要投入關注,雲林提供了全國最大的果菜供銷量,我們每天所吃的蔬果一定有來自雲林的農產品,近來有許多漂鳥青年回歸家鄉參與農業生產,也參加農民大學的課程訓練與實作。 西螺靠近濁水溪,每年雨季濁水溪氾濫時黑土沉積在臨近的鄉鎮,讓沿岸農田獲得最多的滋養。在日本執政時代西螺與莿桐所生產的稻米都是「御用米」直送日本天皇,也造就西螺米食文化的豐富,傳統小吃有九層粿、油蔥粿、碗粿、麻糬、草仔粿、肉粽、鹹粥、米香等。 今年年會慶的地點選在西螺,也是因交通方便且是全國最大果菜運銷公司所在地,臨近有許多農田,可就近參觀以了解食物的來源,而廣興教育學園更是經常提供農業或社區營造等的活動場地,場地設備功能完善,加上腹地緊連廣興國小更是中南區親子團基訓經常借用的場地。年會活動加入小農市集,希望拉近與食物生產者間的距離,多了解農作的生產過程及學習如何選擇安全農產品,當然還有荒野人的特色——自然創作。最重要的體驗活動有分享概念的「石頭湯」,還有食物的料理過程現場操作,「自己吃的食物自己做」烹飪活動一起來,因應炎熱夏天我們還提供了斗六有名的湯圓剉冰。報名住宿者還提供西螺傳統米食小吃,讓大家不用排隊就吃得到哦,歡迎夥伴們踴躍報名,我們雲林見。 荒野雲林分會:鐵馬環島倡議PM2.5 活動-荒野20 週年系列活動
迎風跳躍的音符
原始出處:數位文化電子報 文/諶家強(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風從那裡來?簡單的說,有空氣流動的地方,就會產生風,當空氣流動旺盛時,風力強而有力;反之空氣流動緩慢時,則風力小而緩。風力的有無和強弱,往往和自然萬物的生命脈動息息相關。 在自然界中,除了水中生物外,絕大多數的陸地物種繁衍,小從病菌、真菌等微觀世界,大至昆蟲、動植物,都需要經由風力的傳播,才能迅速的配對成功進而擴展自己的族群,自然界也因此互為消長而生生不息。風真的有這麼大的神奇力量嗎?現在就讓我們來探討這個有趣的大自然影武者。 一、病菌的散播 我們都知道,微觀世界中存在著許多細菌和病毒等危害生命的病菌,細菌需要自行以複分裂來增殖,病毒則趁隙進入生命體中,利用生命體的細胞複製功能來大量的製造分身,雖然兩者的繁殖機序不同,但是都有一個相同的推手,那就是風,風才是唯一可以左右病菌繁殖快慢的決定因素,如果沒有風的幫忙,病菌只能停損在感染者的小區域內,將有助於控制疫情的擴散。病理實驗室在操作病菌吊菌培養時,一定會在密封的工作檯面上進行;為了讓致死率高的病菌無法隨風散播,許多大型醫院都設置有負壓病房,就是這個道理。 二、真菌的拓展 食物放久會變質酸敗,水果過熟會覆蓋黴菌斑,這個現象是怎麼發生的?落葉堆積久了形成腐植土,朽木腐爛則會長木耳和蕈菇(圖一),是不是很奇特?其實這些現象的幕後主角就是真菌。真菌藉由孢子來繁衍族群,孢子的重量極輕又細小,必須在顯微鏡下才能看見。當真菌成熟時會主動或被動釋放無數的孢子瀰漫於空氣中,只要有細微的風力帶動,就能輕鬆的飄散到各處落腳,扮演自然界中最稱職的清道夫角色。如果沒有風的助力,真菌將無計可施,所以若想要食物保鮮或木頭防腐,食物滅菌後密封或木料表面上漆包埋,必然是最好的選項。 圖一.1 褶紋鬼傘(筆者攝) 圖一.2 王也珍.黃金銀耳(來源:典藏台灣) 三、植物的貴人 許多植物的種子末端長有毛絨絨的冠毛,其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藉由風力的帶動下四處飄散,具有冠毛的種子,有如降落傘般的隨風飛舞,其中以蒲公英、酸藤、大錦蘭(圖二)等的種子最讓人津津樂道。除此而外,每當植物在開花期,必然會釋放出特殊的氣味,如五月間的柚子花的郁濃花香迎風撲鼻;世界上最大的花-大王花,開花時奇臭無比,發出惡臭的腐屍味,皆有喜好者循味前來舔食花蜜,順便幫花朵授粉。此時風力的有無,便成為花朵能否成功授粉的關鍵因素,所以果農們都知道,風是植物的貴人,果樹一定要種植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中,才會有好收成。 圖二.1 西洋蒲公英(筆者攝) 圖二.2 彭鏡毅.大錦蘭(來源:典藏台灣) 四、蜘蛛織網的關鍵 雖然織網蜘蛛的蛛網有如天羅地網般,感覺上很紮實,但是仍然很怕強風的吹襲,因為會吹破蛛網讓織網的努力白費,然而蜘蛛織網,又一定得藉由風力的幫助才能成功,兩者豈不互相矛盾?原來蜘蛛織網的第一步,必須先爬到一處置高點上,拉出一條條的細長的蛛絲隨風飄揚,然後靜靜的等待,當其中一條蛛絲纏到四周的固定物上,將會以這條蛛絲為基準,先咬斷其他飄散不用的蛛絲,再由這條蛛絲中央下拉第二條蛛絲,形成賓士轎車的標誌,隨後在四周再找1-2個固定點,連成一個三角形或多邊形,增加輻條,從中心往外結一個稀螺旋網,再從外往中心結密螺旋網,稀網就成了在輻條之間爬的橋,密網一接近稀網,就把稀網咬斷(圖三),最後接近蛛網中心,結網完畢,停在中心等蟲子。如果沒有風的幫助,織網蜘蛛要想成功織網就很困難。 圖三 橫帶人面蜘蛛(雌)織網(筆者攝) 五、昆蟲的媒人 目前地球上已被命名的昆蟲有近百萬種,尚未命名的,少說也有三至五百萬種,數量這麼龐大的昆蟲族群,除了會發聲的極少數品種能聽音辨位外,全都需要一位幫忙傳宗接代的大媒人,那就是風,風真的是無處不在又無所不能,總是扮演最稱職的昆蟲大媒人角色。 由於每一種昆蟲都是雌雄異體,需要相互配對受精,才能夠繁衍下一代,因此各自釋出獨特的費洛蒙來吸引對方,也各自演化出獨特的接受器來攫取空氣中細微的性費洛蒙粒子,尤其是在觸角上密佈著嗅細胞最靈敏,能精準的接收同種昆蟲的性費洛蒙,其中以雄蛾具有發達的觸角最具代表(圖四)。然而光憑釋出費洛蒙而沒有風的助力,僅能影響周遭的同種昆蟲,在近親交配的殘缺基因重組下,勢必會讓族群快速的衰弱滅亡,幸好有風的存在,讓遠在數里外的雄蛾也能接收到雌蛾釋出的性費洛蒙,千里迢迢的飛來密會情人。昆蟲這種使命必達的旺盛求偶慾,固然能生生不息的繁衍族群,卻也讓農家充分利用特定的性費洛蒙來撲滅對農作物有害的昆蟲,生物防治法就是一例。 圖四 斑平毒蛾(雄性。筆者攝) 六、動物的愛恨情仇 風,可以說是陸地上動物的最愛,飛禽沒有風,翅膀則無用武之地;走獸沒有風,將無法覓得佳偶傳宗接代。 每種動物只要達到性成熟期,雌性動物體內的性賀爾蒙將會以各種方式釋出體外,直接或間接的吸引雄性動物前來交配,這種性賀爾蒙無色無味,瀰漫在空氣中,藉由風的動力傳達至好幾公里遠的大地,雄性追求者將會一窩蜂的循味覓蹤而來(圖五),緊接著上演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交配爭奪戰。 風,常是動物們又愛又恨的無形朋友。每當夏日炎炎,動物身上厚重的體毛無法有效散熱,陣陣涼風吹拂帶走一波波熱氣,馬上能消暑降溫,解除脫水中暑的危機,成為動物們最愛的朋友。冬天刺骨的強勁北風席捲大地,迫使動物們久窩巢穴或往溫暖的環境遷移,避免食物短缺又受凍失溫,這點又讓動物們無奈的面對冷風的煎熬。每年侯鳥季節性的遷移和五色鳥的巢穴出入口,一定選在南方(圖六),就是這個道理。 圖五 公狗循味而來(筆者攝) 圖六 五色鳥巢穴出入口朝南方(筆者攝) 七、好風與壞風 基於人們對於風的好惡需求,可以簡單的以風力的強弱分成好風與壞風兩種,好風可以幫助人們完成許多日常生活所需,如風力發電、帆船行駛大海、風扇的運用等,這些都是正面能量的展現,有加分的效果。反之過於強勁的風力,如颱風、龍捲風、沙塵暴和焚風等,則會吹毀地上建物或農作物,造成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這種避之危恐不及的負面能量,往往是人們最不樂見的壞風,自然是大大的減分。 然而壞風有時也能成為好風,要看以那種角度來界定,譬如高山上強勁的冷冽北風,是動物們難以長時間生存的禁地,強風會抑制木本植物的嫩芽生長而形成特有的風剪效應(圖七),枝葉全往南方伸展;在受風面的裸石無法孕育出青苔而顯得光凸殘破,但是有弊也有利,卻可以成為登山客在蓊鬱山林間迷路時,除了羅盤外的最佳天然方位的辨識依據。 圖七 風剪效應(筆者攝) 八、風的鬼斧神功 在自然界中,有許多千奇百怪的岩石造型,從不曾被人類精雕細鑿,在經年累月的在強風細沙風化下,如鬼斧神工般的栩栩如生,無不讓人嘖嘖稱奇,如野柳蕈狀石的女王頭、東北角海岸的風稜石、田寮鄉的月世界等(圖八),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在有心人的企業化經營下,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經常可見絡繹不絕的觀景遊客,無形中幫當地商家帶來不小的財富。 圖八.1 李釣綸.野柳女王頭系列之1 (來源:典藏台灣) (上)圖八.2 陳景容.倒影(來源:典藏台灣) (下)圖八.3 莊文星.利吉泥岩惡地地質景觀 (來源:典藏台灣) 人類知道高速的風力具有神奇的力量,於是發明出各式各樣的器具,利用馬達轉速的帶動下產生高速風力,如空氣電離子切割槍、風槍、噴漆槍等,成為製造業的好幫手。在交通上,利用高速風扇轉動的驅動原理,發明了直昇機、螺旋槳飛機和氣墊船等,讓運輸業更加流暢便捷。自古以來,風就一直扮演著大地之歌交響樂團的總指揮角色,只要輕輕揮動手中的神奇指揮棒,隨便點向大地上的任何一位團員,立刻就能彈奏出一首首活潑生動的跳躍音符。風,是生命的起源,也是生活的動力,具有高深莫測的能量常讓人捉摸不定,每當大地回春之際,荒野間春暖花開、生氣盎然,總有數不清也道不完的荒野新鮮事躍升台面,這就是大自然的影武者——風——最引以為傲的地方。
荒野有情.20有成 2015棲地守護研討會
文/荒野保護協會棲地工作委員會 圖/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20 歲了,回顧這20 年裡,我們在棲地工作上做了許多努力,五股溼地和富陽公園的認養、雙連埤教育基地地委託管理、五十二甲溼地的保育工作、新竹大山背守護梭德氏赤蛙與友善農耕工作、嘉義諸羅樹蛙保育計畫、花蓮馬太鞍溼地保育工作、金門浯江溪口互花米草移除計畫、淡水河流域四斑細蟌分佈和東方環頸鴴巢位調查計畫,以及最近積極開展的榮星花園棲地復育計畫等,累積了不少成果與經驗。 今年7 月25 日週六在臺灣大學共同教學館,協會特別舉辦「2015 棲地守護研討會」,藉由這次的研討會,將守護成果和經驗分享予會員夥伴及關心臺灣環境的大眾,並與相關專家學者及NGO 夥伴們進一步交流研討,展望未來棲地守護的工作目標。 此次的研討會,我們訂定了三大主題:「都市公園生態化運動」、「河川流域溼地生態守護」及「以棲地保育為目的之友善農耕」,除邀請了各主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NGO 夥伴進行專題演講,同時也藉由各分會志工夥伴們的分享,了解荒野在這三個面向所做的努力與成果。 除了室內的研討會外,同時在臺灣大學的鹿鳴廣場上,規劃了戶外的展示與活動攤位,包括生態遊戲、友善農產品展售、自然DIY 創作、荒野20 週年義賣品販售等,為夏日炎炎的舟山路上增添些許趣味。 此外,在研討會隔天7 月26 日週日,荒野並安排了淡水河流域棲地和關渡自然公園的參訪活動,從大稻埕碼頭登船出發,一路參訪華江溼地、大漢溪人工溼地、新北溼地、社子島、五股溼地、關渡溼地、竹圍紅樹林溼地、挖子尾溼地等,讓大家從不同角度領略淡水河生態的美麗與憂愁。 邀請夥伴們一同來參與這場精心策劃的棲地盛宴。 大會手冊:電子書下載/線上閱讀
盛夏的燕會
文/李易芳(荒野臺北分會解說員,自然名:田字草) 圖/荒野保護協會臺北分會 小時候看到的平房,對小小年紀的我而言好高啊!卻遮不了我看天空的視線,藍天白雲下小小的鳥兒麻雀、燕子隨處可見。但曾幾何時我長大了,而身邊的房子也跟著長大,一層一層往上升,看到的天空範圍卻越來越窄。 以前下班途中會經過一片由大自然自己經營的土地,每年春天後會看到三三兩兩出來覓食的家燕,新手燕爸爸、燕媽媽有時低飛,有時不穩定急忙地亂竄,似乎急著回巢哺育。但現在這景觀變少了,這片土地也被高樓大廈給水泥化,常見的鳥兒身影漸漸消失,生活進步也讓人與人之間變得冷冰少了溫度。慶幸在臺北五股溼地被保留下來,它還擁有一片北臺灣最大的蘆葦叢,給予南返的燕群一個穩定安全的飛翔訓練地。 五股溼地的蘆葦叢是北臺灣最大的區域,每年盛夏時期8 月至9 月中旬,會有上萬隻的家燕、洋燕、棕沙燕……匯集於此,白天時牠們會出去覓食,傍晚時分則從四面八方飛湧而來齊聚於上空,我們都戲稱燕群們在做「晚點名」,點名後開始為南返做飛翔訓練。於空中盤旋飛翔,「咻!」的俯衝後又立即升起,升升降降、向左轉後又急速的迴轉向右,展現牠們高超的飛行技術。整個飛行訓練約持續30 分鐘,之後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小黑影會瞬間消失大半,再一轉眼間,天空中只剩下黑暗前的晚霞餘光。 每年帶隊解說時,總在參與的民眾身上看到當年自己那副驚訝的模樣:嘴巴發出「哇!」的讚嘆聲;走在賞燕步道上,擔心天上的燕兒便便會不會掉下來;兩旁的蘆葦裡不時的飛竄出小黑影,擔心牠們會不會撞在一起。這場自然的飛翔秀比炫麗煙火秀來得樸實卻壯觀,如果你來不及參與過去的燕群花火秀,今年一定不要再錯過。 今年春天你在屋簷下見過燕子了嗎?穿著燕尾服的牠跟我們打過招呼,築巢繁衍後的一家人將在不久後的日子集結成群,準備南飛。看過這場盛會,你一定會被感動,當心被感動有了溫度後,你也會關心起這片土地的一切,與我們一起守護這片壯麗的自然景觀,一起愛護這片成長的土地,珍惜著大自然送給我們的寶藏。 今夏這場盛會即將來臨,你/妳準備好一起與之共舞了嗎? 活動報名
環保,在生活中反覆練習
文、圖/荒野保護協會 2015 年荒野地球倡議行動特別與「IC 之音.竹科廣播」合作,從三月至五月隔週四下午,荒野夥伴與主持人袁常捷,在空中與聽眾分享環境保護經驗,透過專業的媒體廣播電台,錄製一系列與土地對話的主題:地球一小時行動、餐桌上的氣候變遷、都市公園生態化、地球日棲地大調查、諸羅樹蛙保育計畫、海洋守護行動。六個不同的題材,喚醒民眾守護環境的意識,一同改變日常生活態度,實際參與環保行動,並將與自然共存的觀念傳播給更多的民眾,期望聽眾能成為影響社會的力量。現今環境保護觀念已成為普世價值,然而棲地守護是一場永不止息的行動,每個人每天只要花一點時間、花一點力量,在生活中反覆練習,學習尊重自然、與之共存,臺灣的自然環境就能一點一滴被守護下來。 未來荒野將持續與優質的大眾媒體合作,共同推廣環境保護理念,邀請民眾一同參與,也期盼大眾能支持友善環境的媒體,從凝聽分享中學習、改變,為自己也為下一代盡一份心力。 節目名稱:親愛的生活練習 撥出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17:00-18:00 主持人:袁常捷 認識「IC 之音﹒竹科廣播」 I Care. I Can. I Change! 全球華人的心靈故鄉 IC之音﹒竹科廣播成立於2002年,是由服務於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菁英,秉持「我在乎‧ 我能夠‧ 我改變」的理念,為提升社會向上、向善的正面力量,創辦「以公益為目標」的商業性電台。 IC之音期待以人文內涵和優質輕鬆音樂,喚起電台發射服務之地─桃竹苗社會的人文情懷;與聽眾分享科技、財經、產業最新資訊,同時反思科技對環境、社會的影響;進而將正面的心靈價值推及全臺灣,以至全球華人世界(如圖)。 超過十年深耕,IC 之音已成為桃竹苗地區最受歡迎的專業頻道、知識工作族的標準配備,也是全國最受肯定的科技人文優質電台。 全國唯一三度榮獲金鐘專業頻道大獎的優質電台 過去在廣播金鐘獎,評選電台整體表現的大獎「專業頻道獎」中,IC之音‧ 竹科廣播FM97.5是全國唯一三度獲獎的廣播電台,創下空前紀錄!2014 年,IC之音於四年間三度入圍企劃編撰獎,兩次獲得大獎,呈現IC 之音圓熟的企劃能力,是企業共創社會責任的最佳選擇。【愛上新竹】節目及主持人潘國正、洪惠冠連續三年獲獎,也展現了IC之音對土地、對人文的關懷。開台以來,累計獲得二十座金鐘獎殊榮。
水泥業重回西部?亞洲水泥(關西廠)將率先闖關!
文、圖/陳香靜(荒野新竹分會鄉土關懷小組,自然名:笑靨花) 90年代西部礦區劃為保留區 水泥業在臺灣發展至今已有八十三年的歷史,產能由最初的三萬公噸增至目前的兩仟多萬公噸;1984年,經濟部為因應西部水泥礦源之耗用量甚鉅,其他水泥主要產區(高雄壽山、半屏山、大岡山等地)礦源已日漸不足,又鑑於當時人民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使得設於西部人口稠密之水泥廠,屢遭居民阻撓,而恐有遭致停工命運,政府遂將水泥產業大舉東移,並在90年代將西部礦區劃為保留區。 經濟部於2009年9月24日公告劃定新竹縣轄區內石灰石礦業保留區,然而此政策卻在水泥業者的壓力之下,於2013年4月急轉彎,無視脆弱山林,解禁西部礦區。 臺灣水泥現況 我國水泥生產量長年「供過於求」已是不爭的事實,水泥產能過剩、供過於求、外銷量與外銷率高的情形依舊(亞泥水泥外銷率已長年達30%以上),直至2014年外銷量仍高達3,496,168公噸(表1)。我國早已開放水泥進口,2014年的水泥進口量高達1,472,184公噸,臺灣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的水泥。 水泥業於西部捲土重來 2013年4月1日解禁西部礦區保留區後,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徐旭東)、礦區所有人(羅慶仁及羅慶江)即重新申請石灰石礦採礦權,並取得礦權後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使用,通過申請環評標準,因而進入環評程序,身為西部復礦第一起案例,同時也為近年來整體開採面積最龐大、離聚落最近的採礦案,亞洲水泥在西部捲土重來備受各環保團體的注意。 然而我們卻發現亞泥將開發案切割成三案,企圖混淆整體開發影響之評估。此舉引起荒野新竹鄉土關懷小組、綠黨新竹縣議員周江杰(江杰並為荒野夥伴)、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環保團體於6月4日集聚環保署前,抗議亞泥切割環評,並呼籲環保署應依環評法第15條,將同為供給亞泥生產的三個採礦案合併審查,三個採礦案分開審查,並無法減少整體環境污染的事實,開採後大量的揚塵、地表裸露對當地空氣品質、承受水體與生態環境的衝擊更不應切割計算!(資料來源:綠黨、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表1:全臺水泥生產及銷售表 項目別 生產量 銷售量 內銷量 內銷率 內銷值 直接外銷量 外銷率 直接外銷 2011年 16,852,035 17,422,904 11,425,821 65.58% 23,519,473 5,997,083 34.42% 7,403,960 2012年 15,807,591 16,285,744 11,238,336 69.01% 24,387,126 5,047,408 30.99% 7,942,449 2013年 16,553,533 17,191,928 11,262,603 65.51% 24,594,014 5,929,325 34.49% 8,714,379 2014年 14,591,672 15,194,053 11,697,885 76.99% 26,244,069 3,496,168 23.01% 5,516,474 單位:公噸,新台幣千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製表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謝孟羽律師 環評會議 環保署於2015年6月4日召開第一次環評會議,荒野新竹鄉土關懷小組針對此復工案提出以下疑慮及陳述。 (一)生態恢復 5月22日現勘時,當地居民的陳述:二十年前亞泥在當地開採所產生的棄石,目前仍堆置在關西金山里的一座小山丘上,這些棄土造成了山丘下方居民住家旁的檔土牆的龜裂和土地的滑動,有安全上的疑慮,害怕成為第二個小林村;當天夥伴親眼所見,停採的這十九年來,當年開採地區仍有多處裸露的狀況,生態實尚未完全恢復。 水泥開採乃屬於高破壞式炸山開發,凡地表上的動植物需一律剷平。業者承諾將做好植披綠化工作,並在開發期間在每一開發階段將樹木作妥善的移植及種植的工作,然而,正確的樹木移植相當耗時費工的,山林恢復生態談何容易?生態要達到平衡有其複雜度並需長時間蘊釀,而非業者簡單買樹苗做人工造林就做得到,更何況是高破壞式的炸山開發方式,土地恢復更是不易。 (二)用水問題 水泥產業為甲種污染性工業,是十分耗能及污染相當嚴重的產業。礦區一旦復工其承受水體之污染及帶動下游水泥業的用水應全面評估,業者表示申請區內不計劃洗選礦石,無需抽地下水也無水權問題,但規劃書卻寫著若未來有用水需要,礦區所需用水將取自其建蓋水塔裏的天降水或滯洪沉砂池的積水,若仍有不足則買水車的水來供應。今年的水荒問題限制了農田的用水,乾旱限水的問題已使政府和民眾感到焦慮,如今又多了一個高耗能的產業來搶水?若逢乾旱限水期,水車裏的水那裏來?不當乾旱造成限水,水是先給農田、民生、公共用水使用還是給生產總量在臺灣已經過剩的水泥工業呢?開採時產生大量揚塵的問題,業者必需灑水以減緩揚塵造成的空氣污染,同樣的問題,水從哪裏來? 不僅僅是上游開發開採的耗能問題,一旦重啟開採,下游的水泥工廠(亞泥橫山廠)生產復工後,用水量亦跟著增加,因此用水評估,委員們應站在全新竹的高度考量新竹整體水質水量供應情形,而不是僅僅以業者申請的這28公頃用水量來評估。 最後,在臺灣水泥總量生產過剩的前提下,希望環評委員仔細考慮是否有必要重新在西部啟動一個高耗能、消耗國土的產業。
自然建築 回歸與創新
文/林雅茵(荒野保護協會志工、林雅茵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本文刊登於《營建資訊379 期》 家是幸福的根本。有一個安穩的託身之處雖不一定就會感到幸福,失去安全的居所卻很難有幸福可言。在地球上各個角落,從古至今,人類的居住空間歷經長期演變,出現過各種不同的建築型態與居住型式。 非洲的圓形土屋 柬埔寨的水上人家 工業革命以後,環境變化加劇。對於筆者的祖父母和曾祖來說,家是三合院、土墼厝、竹攏仔厝、瓦房或磚仔厝。然而,才不過短短四、五十年,家的面貌已經全然改變。 三合院 自然建築 應時而生 1960 年代是一個反省的年代。在西方,人們開始思索現代物質文明帶給社會,乃至於每一個個體的影響。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自然建築」運動應運而生,重新檢視「居住」這件事情。「自然建築」一辭源自英文「Natural Building」,是國際自然建築運動的通稱。其主要內涵是就地取材,以自然材料或回收材料、傳統或創新的工法、手工為主的方式,來設計與營造建築物。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回歸於自然。 那麼,自然建築和古代人蓋房子,以及現代的綠建築、自力造屋或是協力造屋,究竟有那些相同或不一樣的地方呢? ● 取之自然、回收利用、手作勞動 土、石、灰、木、竹、籐等,只要能找到人力與成本上可行的方法來處理原材料,並使用於適當的部位,則無材不可用。以竹子的應用為例,國際上這十幾年來將竹子視為一種可以解決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的重要綠色資源,高度加以關注。然而在臺灣,多數人的印象仍停留在竹子就是窮人的木頭這樣的概念上,與竹子相關的產業也大多式微。竹子原是臺灣最豐沛的自然資源之一,因此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窮人的木材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高度關注的綠色資源 從工法來說,土,全世界都有,各地用法類似卻又巧妙不同,今昔又各有春秋,臺灣早期民居常見的有土墼、編竹夾泥、版築等工法。不唯土是如此,大凡自然材料皆然。國外近年流行一種Straw Bale 工法,以純乾草壓製成長條塊狀材料,疊砌成牆,再於表面依次糊土及抹灰保護,施工快速,規模可蓋到物流中心的大型倉儲。 事務所在臺東阿牛村蓋了一棟土房子。這個案子最大的特點是使用自然材料。基礎採用水泥漿砌塊石,也是整棟建築物唯一使用到水泥的地方。牆體以地基挖出來的土加上稻草、砂和水,用捏黏土的方式就可以蓋起來,結構上屬於承重牆系統,惟臺東位處強震帶,因此仍用了柳杉圓木伴同支撐屋架。此外也使用從後山採下來的莿竹,剖成竹篾,編成骨架,抹上泥與石灰,作成臺灣傳統的編竹夾泥牆。屋架部份則使用孟宗竹與桂竹,採用藤皮綁束的工法施作。地坪以地基挖出的火山凝灰石碎塊作防潮層,面層為純土造。土地板堅實而溫潤,調節室內溫濕度的能力非常好。牆面以灰作處理,拌和現地的椰子纖維使用,局部施以泥塑增加空間趣味。這棟小小的土房子,前臨太平洋,背倚都蘭山。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之間,看起來並不顯得突兀。 原木鑿榫頭 竹子與藤皮綁出的屋架 土地板 阿牛村土屋 再舉營造中的中壢有機生活作坊「聚福園」為例。這個案子最大的特點是「能揀的就不買,能買二手的就不買新的,要買新的就要買有意義的材料」。用二手木料可搭出花架,也可將小料組成大料,再用傳統工法搭出屋架。 友善土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除硬鋪面,讓窒息的土地重新呼吸。於是將柏油與混凝土鋪面打除,改換成紅磚襯墊砂的透水工法,並收集屋頂的雨水為水源,在打開來的土地上作一個生態池。目前已經有青蛙入住,未來將作為生態觀察解說的重點。挖除的柏油送去回收再製;打除的混凝土塊、紅磚塊、石塊經過分類成為級配料與土椅基座;使用三和瓦窯的尺磚,裁切的邊料可以手製馬賽克。 灶是一個家的靈魂。遂請來當地的老師傅砌了一個大灶。學員的中餐,從摘菜、學習生火、用大灶煮飯開始…。 廢木料挖寶,回收再利用 打除混凝土鋪面,讓窒息的土地重新呼吸 雨水收集再利用的生態池 打除的混凝土塊成為土椅基座 裁切的邊材可以手製馬賽克 ● 不只是建築外殼還要創造能資源循環 自然建築關注處理的不只有建築物,還應包含周邊土地上生活所及的範圍以及必要的生活設施,因此不單在造一個外殼,同樣重要的是創造生活中的能資源循環,讓來自土地的,回歸土地。具體的作法有廚餘及落葉堆肥和菜圃甚至雜排水的結合設計、乾濕分離的生態廁所、人工溼地污水處理系統、人力揚水設備、太陽能與風力發電設備的應用等等。 糞尿分離式生態廁所 土製的麵包窯可算是西方 自然建築的基本配備 ● 就個人而言 自然建築的先驅者,Ianto Evans 先生說:一棟房子應該像一件衣服一樣合身。以滿足基本需求的最小空間尺度為原則量身訂作。又說物似主人形,什麼樣的人就會蓋出什麼樣的房子。 自然建築和古代人蓋房子最大的差異在於,這是經過有意識的反省之後的積極行動,不同於古時候是隨順外在大環境下必然的結果。其價值非僅止於以自然材料及工法蓋一棟房子,在更根本的層次上,簡單生活、規律的勞動、將個人的生活作息融入自然循環之中,方為其精神所在。 具創造力的勞動,可以為身心注入正向力量。Dignity Village 是美國波特蘭的城市修復計畫。在志工的協助下,讓遊民動手為自己蓋房子,改善生活,重建身心,將一個原本髒亂危險的區域變成一個欣欣向榮而有特色的社區。 Dignity Village ● 就社會而言 協力造屋經常出現在自然建築活動當中,以互助合作取代單向消費,可以廣結善緣,增進人際和諧。 ● 就土地而言 自然建築希望能做到愛物惜物、低耗能、無污染、零垃圾與共生,使建築及其相關行為從根本上自淨。因此在營建方式上希望跳脫工業化材料無法以原貌回到自然界大循環的問題,以及大型施工機具對土地粗暴的對待方式,從而使建築物在其整個生命週期當中不對土地造成污染,並於其生命週期結束之時不給地球留下垃圾,或儘可能留下最少的垃圾。 逆勢而為 抑或順天應人 然而,以前看來很難的事情,現在做來很容易,反之亦然。 幾十年前從臺南到臺北坐車要一天,現在搭高鐵不要兩個鐘頭。 以前土地很乾淨,現在要找到一小方淨土非常困難。 大環境不同,逆勢而為是困難的。然而現代生活是建立在無法永續的基礎上,各種警訊告訴我們,資源條件及物質環境不可能一直這麼充裕。當時候到來,我們是否仍保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呢? 為什麼在工業發達的現代,要做看起來像開倒車的事情 或許有人會問,自然建築是在開倒車嗎? 筆者如是想:科技進步帶來的未必盡是好處。 以前人蓋房子可以等茅草、等竹子、等樹木,等材料生長到最適宜採收的時間,但是現在混凝土拆模常連14 天都等不了。可惜的是,老祖先們用千百年的時間所累積的,具有美感的古老技藝與建築智慧,在現代工業化過程中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消失當中。速度改變了這個世界,其結果不能武斷地論定好壞,卻值得重新審視與反省。 我們常覺得現代人的生活缺乏意義,這其中很大一部份原因來自於人們不知道周遭物品的來歷,既無瞭解,自然不會有感情,也因而能夠輕易丟棄。然而當最終擁有了一棟自然建築時,通常表示我們非常清楚這堵牆裏的稻草是七月半豔陽天下揮汗如雨地綁紮回來的,也知道那樘窗戶的玻璃是誰家拆下來的。那代表著屋主對這棟建築物所用的材料可以如數家珍。 勞動讓人身體健康、精神強健,又可讓人住得健康又自然。 現代人類的建造活動大大地改變了地球表面的景觀,雄偉的高樓大廈比比皆是,綜橫交錯的道路系統上天入地,有高架的高鐵,也有穿梭地底的捷運。然而在我們住得越來越安全舒適的同時,各式營建廢棄物正以驚人的速度在我們的腳下堆積。良田與埤搪經過了我們這三四代人的手裏,似乎並不打算留給後代臺灣人,臺灣的農地被當作建地買賣早就是常態。無節制的營造活動是破壞土地的元凶,其危害比農藥與化肥更烈。自然建築相較於現代建築最大的差異,在於建築物當生命周期結束後能很快地塵歸塵,土歸土,不給地球留下巨型垃圾。 現代的建造活動,讓地球表面大為改觀 未來課題 從作中學 倘欲使自然建築重回常民生活之中,需要進一步提升材料前處理與施用工法的成熟度及可操作性。未來針對自然材料的潛力、結構特性與耐候性必須加強嚴謹的學術研究,並取得必要的實驗數據驗證。自然材料及工法的適法性亦須同時研究與推動。此外,在臺灣,關於自然建築或傳統材料工法的學習一直沒有全方位有系統的途徑與方法等,關於自然建築尚有很多重要課題亟待有心人一起耕耘。 那麼,什麼樣的人適合做自然建築呢? 應該,是能在流汗勞動中找到樂趣的人。想施作自然建築的人,在時間或預算上至少有一項要非常充裕。體力並非絕對的門檻,只有毅力是不能少的。 缺乏經驗的自力造屋者有什麼學習與實踐途徑? 臺灣相關資源較缺乏,但是有心人一向可以透過努力自我進修而具備主導能力。導入專業者開設的工作坊以協助起步是一種有效的方式。經濟上較充裕但是沒有足夠時間的人,則可以藉由點工推動工程進度。在工地環境建構完成後,針對某項低技術,重覆性高而需大量勞力的工作,自力造屋者可於掌握施作要領後邀請志工協力營造。 簡單生活 體現價值 平埔老師傅村伯告訴筆者:以前他們只要有竹子有茅草就能過下去。想想確實如此,有得吃、有得住,人類生存所需原本很簡單。 自然建築運動之所以成形,繼而形成一股力量,主要並非為其雖古猶新的獨特建築方式,更不為製造更多的建築物,而是為了作為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整體生活實踐的一部份,從而體現簡單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回到原點不是開倒車,而是為了構築我們共同的未來。 延伸閱讀:大愛電視台【人文講堂】回到原點構築未來-林雅茵